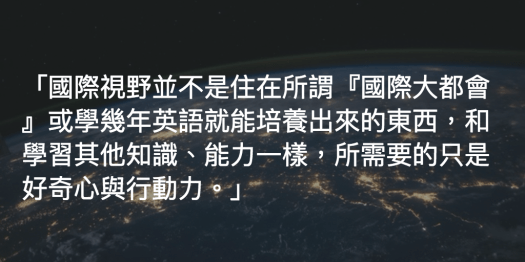那曾經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城市,曾經有一堵牆隔開了同一片天空,曾經有一個狂人從這裏指揮著讓全歐洲陷入恐慌的軍隊。但在遇到的人身上、在整個城市裏,我卻看到他們更多的包容、更多的反省。
有次和一家遊戲公司開會,推銷公司的產品。問起了那公司平時的翻譯流程,負責人說公司的翻譯大都是公司團隊自己完成的,他們一百多人的團隊來自二十多個國家,能說十多種語言。她說大部份的國際用戶的問題都能內部解決。我也好奇地問她是哪個國家來的,她說:「波蘭。」
在柏林見過的公司大都如此,團隊幾乎有一半以上都不是德國人,產品的前期多語言版本大都能靠團隊自己完成。這融洽的多樣性我只在《重慶大廈》一書裏感受過。
認識了一個曾在台灣留學,現正在柏林修讀「國學」的德國人。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;他對中國近代的歷史比我還清楚。
閒聊間他提起以前有人問他:「那你是日耳曼民族嗎?」他說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民族,他不理解民族作為區分不同人的作用。
我接著問他:「那你有因為德國人的身份而自豪嗎?」他說這問題在德國有點敏感,因為答案要不讓人想起「不愛國」,要不就想起二戰時的極端民族主義,很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爭拗。每次聊到中國相關的問題他都先問我會不會介意,他怕我也是把「國家」放在心中很高的位置那種人--有時候會對問題偏向盲目且麻木。
他是我第一個遇到認同我說「國家」、「民族」這些概念不過是當權者把人分群以易於統治的人。他也是自由主義的擁護者,他也厭惡因為「國家」、「民族」、「宗教」分歧而引起的戰爭。「我爺爺當年是德軍的士兵。」他說道。我沒有再問下去。
從猶太屠殺紀念館到柏林圍牆遺址,還有朋友分享他小時候所受的教育,我看到了沒有逃避錯誤;沒有找借口;還積極找方法改善的一群人。